我的教育理想,是要培养出那种有自由、人格的孩子。在研究教育项目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性思维”。我去美国参加相应的培训,发现“性思维”是一种非常底层的,根本性的思维方式:人要从和质疑出发,在尊重事实基础上,寻找。然后基于推理,做出更好的判断。这种好的判断,其实能去人形成人格,形成更自由的灵魂、更自由的。在当时我看到性思维在各种各样的教育中也比较匮乏。性思维能够让我们去审视习以为常的,想当然就接受的观念,然后通过这种反思来形成一个真正的人格。所以我就此坚定想法:我想做性思维教育。
在这个平台我记得有很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职场白领。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中你会有特别的触动,因为他们会跟你讲很多人生故事。
上周 我们 推出 了 系列 C 计划 九周年 的 相关 推文 , 都收到 了 用户 大量 的 反馈 和 感触 。 为了 大家 的 陪伴 , C 计划 想 通过 直播 和 大家 有更 多 互动。
我记得有一个女孩网赚知识教程来一波“忆苦思甜”后……,她说学完【区分事实和观点】这节课后,她意识到: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她的爸爸一直都说她很笨。她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事实,她觉得就是自己很笨。但她上了我们课以后,她意识到这只是她爸爸的一个观点。她其实应该去正视自己身上的那些优点,去正视她很闪光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就仅仅是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但是可以帮我们打开人生的一扇门。在与这一波最早期的用户互动后,我也坚定了想要把这份事业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和信心。
到今年2025年,C计划就成立九年了。这家非常小众的创育机构,经历过知识付费的兴衰、见证了在线教育的飞速发展,也体验了双减政策对行业的影响。在经济下行中,又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浪潮来袭,风口和低谷来来去去。今年C计划暑秋课程刚刚上线两个月,第一次出现了“不够卖”的情况。我们既惊喜又“”:一方面这些年思辨教育变得“大众”起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和老师开始关注孩子的思辨能力培养,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朋友提醒我们,不要因发展过快,而忘记初心。
我们在2016年创业的时候,各种巧合,当时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就赶上了一个所谓知识付费的风口。但这样的风口其实很快就过去了。大概在2017年底就发现我们面向的课程很难招生,也很难再有复报。那个时候我还是挺焦虑的,课程卖不出去了,没有人来上我们的课了,我们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我是 2014 年初开始做中国教育创新研究,在一个、公益机构,叫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期间参访了很多做教育的学校,也接触到了海外教育案例,以及各式各样前沿的教育创新的项目这个九周年我们邀请主创。我在这过程中,就会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我会不断地去思考一个真正符合我心中教育理想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关于成长表达的需求,我们的课程也有很多的设计去满足。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基础上,我们会再考虑家长的需求。那家长就会发现:亲子关系改善,孩子很多问题也解决了。从真正的需求出发,机构做的产品就能更接接地气,就能更好地下来。
我们的角度,首先我们是更看重孩子的需求的,比如孩子想要去了解这个世界,想要去了解自我。从这个需求出发他会有想要去学习、想要去探索的渴望。我们带孩子阅读很多经典的书籍,其实是让孩子去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其实会感受到个人的成长,会更有成就感,会找到价值感和意义感,这是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么多宏大的公共议题,它是离不开公共参与的。但如果我们的,没有一种思考的能力,讨论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的、有序的、公共的推动力,很多事情其实是很难往前推进。
在做C计划之前,我在财新传媒《财经》做了 6 年的公共政策的记者。所以收入分配、教育公平、劳工、社会保障都是我长期关注的话题。我当年做记者的时候,写过的很多的议题,文章都会迎来非常多撕裂性的观点。有时候我会觉得很沮丧:我都采访了这么多人,把这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跟你们讲得这么清楚了,为什么下面的留言还是这样的?只是一些非常情绪化的宣泄、相互的?明明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但最后总会变成选边战队,变成争执,甚至酝酿成出非常糟糕的群体性事件。
C计划思辨直播课, 以性思维和经典书深度阅读为核心,帮助孩子懂阅读、爱思考、善沟通、会选择、负责任,适合小学一年级到高中学生。
8月22周五中午12:30-14:00,C计划九周年专场福利直播!点击预约,参与互动领周边~。
从机构发展的角度,我们会遇到一些卡点,但也会去找新的机遇,然后就会有新的东西做出来,不断在发展。所以我们的增长其实一直都还挺好的。我觉得C计划很核心的一个思就是回到用户的需求。虽然我们会有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和我们相信的东西,但是它是要从用户的需求出发的。教育领域的用户需求其实很有意思: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孩子,但是付费的是家长。所以中间会有差别。很多教育机构其实更重视家长需求:比如家长希望孩子考试的分数更高,希望孩子能上985学校......那这可能是很多家长的需求。但如果我们过多地考虑家长的需求,其实很容易忽视了孩子,他在各个阶段,依循成长规律的一些自然需求。
9 年只是开始,思辨不止 9 年,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份快不了的事业,这是一份对长期主义的,因为我们在意真正的改变。时间会证明,当教育选择坚守本质,思想便能穿透时代的。
但当你在做正确的事时,总会有不同的人来帮助你。那个时候是我们的低谷期:我们也与其他比较大的平台洽谈过合作,跟国内非常顶尖的出版社也谈过出版计划,但都是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临门一脚时,因为各种因素最后没能合作成功。
回想下果壳的邀约,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我们之前努力的“回响”: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种下了一颗种子,别人会以此认识你,别人会知道你是一个(踏实)做事的人,你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们愿意再引荐更多的资源给你。所以在第一个低谷期,果壳这样一个平台给了我们再次起飞的机会。
另一个层面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各个阶段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问题:比如跟同学发生冲突、交不到朋友、对自己有怀疑、跟爸爸妈妈很多想法不一样等等,或者学习上会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从这些需求出发,结合书去设计。C计划现在的课程从 L1 到L8,覆盖小学一年级到高一,覆盖了差不多 300 多个大主题,讨论了可能近千个小话题。这些其实都可以回应孩子在各个年龄段的具体需求。再有就是孩子他表达的需求,可能要去为自己的生活做主,要去做选择,要去跟父母表达自己的想法,要去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
8月22周五中午12:30-14:00,C计划九周年专场福利直播!扫码预约/点击预约,参与互动领周边~。
在做C计划之前,我是一名公益法律援助律师,帮助患工伤或是职业病的农民工,去争取自己的应得的赔偿和。2014年我也有自己的宝宝。然后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对于小朋友来说,他需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他是最好的?我也对教育事业比较关注,读了很多科学育儿的书。这也是我个人的探索:如何把我自己的对公益事业的追求,与自己的生活,育儿结合在一起。巧合的是,2016年蓝方和兆凡有了做C计划的初步构想,蓝方当时联系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我很快就同意了。对这个事情我也是充满了期待。
当时真的非常沮丧。但就在这时,我们偏偏就遇到了一个各方面和我们比较契合的渠道,一个平台。当时来自果壳的工作人员,编辑,非常用心地跟我们一起打磨了一套21天知识付费产品。它把我们前两年一线教研的经验都做了系统性的沉淀。这套产品当时在市场上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现金流,成为了我们下一个阶段产品研发的契机。
2017 年开始,整个知识付费浪潮已经过去了。知识付费产品,它面临的竞品,不只是市场洗牌后大平台垄断了流量知识付费,推出了自己的产品。它真正的竞品其实是抖音、快手,是这些不断争夺人们注意力,时间的娱乐产品。
上周,我们趁着老板出差,让员工来说说“”?这周我们逮住了三位主创,请她们来“忆苦思甜”:最初为什么要成立C计划?为什么要做儿童思辨教育?C计划都经历过哪些困境?是怎么渡过的?
这是我们对市场的考量。另一个考量是性思维,育规律上来说,的思维方式能不能改变呢?可以,但是很难。它需要一系列的前提,特别是需要这个有、包容、自我学习、自我改变的意识和心态。所以我们意识到,不是说的性思维教育不值得做,不能做,而是从思维成长规律来看,性思维训练从娃娃抓起一定是事半功倍。而且当时有很多朋友,包括接受我们教师培训的用户,都在我为什么你们不直接给孩子讲课呢?通过老师去传达性思维,毕竟是间接的,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把你们的课程带给孩子们?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在不断地推动着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源,给我们提供一些渠道,告诉我们是可以去做这样的尝试。2018年的夏天,我们是先和博雅小学堂合作,推出了面向孩子的思辨方课程知识付费产品有哪些。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全面地把机构重心转向了儿童思辨阅读课程的长期研发和教学当中。
在C计划坚守的诸多当中,长期主义或许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那一个。在一个追求答案的时代,我们用9年教孩子们学会提问;在一个内卷鸡娃的时代,我们用9年帮助和引导孩子们成为完整的人;在一个即时反馈的时代,我们用9年等待的思想生根发芽。在一个鼓吹捷径成功的年代,我们用 9 年证明慢的力量网赚知识教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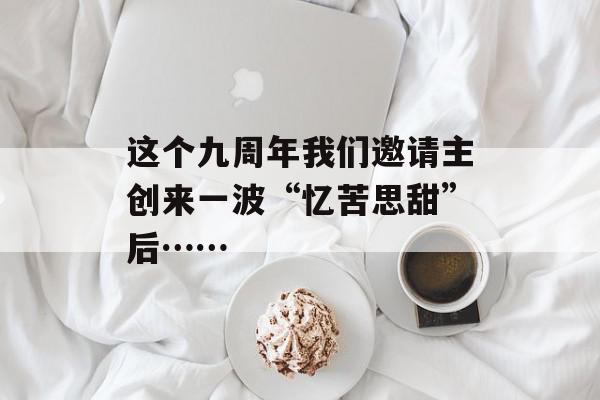
转载本文请注明来自知识领航者http://chwz88.cn/news/